上帝嘲笑每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是,如果没有那些人,也许人间不值得。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90年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前,我最后一次去外滩,那里的东风饭店被改造成了沪上的第一家肯德基店。我们几个同学从五角场骑着自行车去,排了一个小时的队,花1.2元买了一根冰淇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冰淇淋,以至于到今天,我都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淇淋是肯德基的。
那时的外滩边,都是一对对的小情侣在看风景,号称“情人墙”。我们像小流氓一样地吹口哨,赶走了两对情侣,然后,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看江上的水泥船。对岸的那个地方叫烂泥渡,据说要被开发成一个浦东新区。

2019年,我拍摄《地标七十年》,特地叫上老同学秦朔回到了我们当年吹口哨的地方。身后的肯德基不见了,变成了华尔道夫酒店,眼前的浦东,高楼如林。
江风应识旧少年,无非青丝暮成雪。
一
进新华社,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做一个大型调研“百家大中型企业自主权落实现状”,两个月里要跑七个省份、一百家工厂。师傅付上伦临行前只交代了我一句话:“当记者的腰板要直,记住,见官大半级。”
跑到沈阳的时候,已经发现国有企业体系如泥潭巨人,举步维艰。我们请沈阳体改委推荐一家典型工厂。拨通厂长的电话,那头是一个咆哮的声音:“你们还来个屁,工资都发不出了。”
我写的第一篇有全国性影响的报道是《百日兼并》。1991年夏天,杭州一家叫娃哈哈的儿童保健品公司并购了全国第七大的国营罐头企业杭州罐头厂,仅仅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就扭亏为盈。这个长篇报道发在《解放日报》的头版,还配了评论员文章。两个多月后,邓小平南巡,国势为之一变。

1991年,我和报道组同事
十年后的2001年,娃哈哈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饮料企业,我写了一本《非常营销》,成当年度最畅销的企业类书籍。又过了六年,娃哈哈与达能因股权发生激烈纠纷,宗庆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动民意,我颇不以为然,在FT中文网写了一篇《“受害者”宗庆后》。宗先生有好多年不理睬我。
后来发现,要当一个好记者,不得罪人恐怕是做不到的,但只要秉性纯正,时间久了,人心自见。我还写过一篇《“病人”王石》,揣测王石有桑塔格所谓的“病人情结”,据说王先生刚一读到时也不太爽,几年后万科创业二十年,王石辗转找到我,一起出版了那本发行将近一百万册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
写《大败局》,是一次没有预谋的创作。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我发现很多风云一时的企业相继爆发危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营企业的集体危机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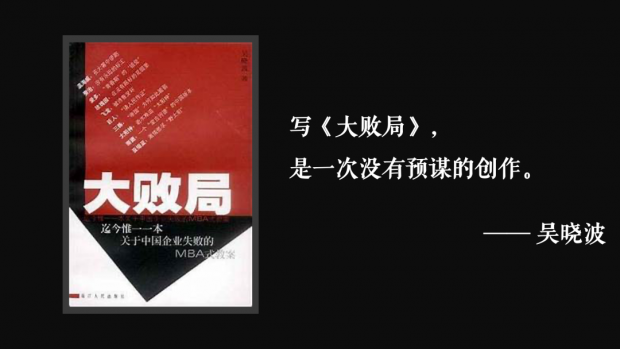
当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泰坦尼克号》,小李子貌美如花,在冰冷的海水里为爱情挣扎。我写了一篇《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全国报刊纷纷转载。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社长见到后,约我把它写成一本书。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书稿既成。我问责任编辑,会打官司吗?她盯着我想了一下说,也许会吧,你怕吗?我说,怕的。在当年,名誉损害官司最高赔50万元。我准备了50万元,然后请了一个律师当《大败局》的法律顾问。
《大败局》发行几年后,我见到瀛海威的张树新,她有点抱怨我在悬崖边的时候又推了她一把。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骄傲的女生,只好强词夺理:“你看,如果没有《大败局》,很多年后谁还会记得瀛海威呢?”树新猛地莞尔一笑:“那今天的茶看来还得我请了。”
二
相比《大败局》的偶得,《激荡三十年》就是有预谋的了。
2003年,我离开新华社,一时间无所事事,就受邀去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当访问学者。在那里,我明显地意识到美国学者对迅猛发展中的中国的好奇和陌生——其实,这一事实到今天仍未改观。于是,我动了写作一本当代企业变革史的念头。

写到一半的时候,王石来杭州看我,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父亲是官员,我母亲是锡伯族农民,那么我,以及我们一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我当时正接触到南通张謇、无锡荣家的一些资料,转念一想,索性再往前写吧。就这样,我跑去招商局的档案室待了一星期,然后去北碚查卢作孚,赴天津访范旭东,往福州看船政局,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站调张公权和陈光甫,再七手八脚地去历史书里扒拉古代商业的蛛丝马迹,相继写成了《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从2003年动念写“激荡”,到2013年“历代”出版,这十年冷板凳坐得我好辛苦,也很快乐。在大学的时候,立志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像李普曼那样的记者,访名人、开专栏、写书,用文字与世界打交道。专注商业世界后,觉得当一个德鲁克或小钱德勒也挺好的,站在岸边不湿鞋,做一个“介入的旁观者”。
再然后,到了2014年,我停掉所有的专栏,开出了吴晓波频道。
三
很多反对我办频道的,都是我的亲密朋友们,有师友、读者和学生。
他们最看重的是“清誉”两字,金钱是个“阿堵物”,说出来都嫌脏,何况亲身下海去博取。
第一次隐约意识到,我与原来那个圈子里的人们发生了很难弥合的裂痕,是王五四写了一篇《吴晓波老师,你的情趣内衣露出来了》。他说,“吴晓波拼命想兜住精英们的底裤,没想到自己的情趣内衣却露了出来,我只能说在救赎社会的道路上,中国的精英们得先完成自我救赎,你们曼妙的身姿,或许在给乡镇企业家上课时才会有发挥的空间。”
在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他对商业的鄙视和对企业家群体的嘲讽。中国这一代文人面对商业时的“耻感”很神奇,好像一块跷跷板,高的一头对别人,低的一头对自己。

五四的这一姿态在知识界并非孤例。我很尊敬的资中筠先生也曾认为:“我原来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
这样的论断在我看来,是不能认同的。因为,当代企业家群体的“软弱”并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公共治理现实下的扭曲性投影。进而言之,正是对中国商业进步的漠视和不了解,造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自我撕裂和彼此失望。
汉娜·阿伦特认为,“在二十世纪的大环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在当代中国,唯一具备了“革命”特征的,正是商业世界的突变,知识阶层对之的隔膜和拒绝深入研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或许,你认为我的这个论断很“犬儒”,但是,我并不试图改变。
在创办频道之初,我拟定了我们的价值主张——“认可商业之美、崇尚自我奋斗、乐意奉献共享、拒绝屌丝文化”。这几年来,风雨飘摇,我们一直在这里,乐此不疲。
我们思考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并参与问题的解答和试验。最终给我们以结论的,竟不是我们的朋友或敌人,而是时间。

也许在六年前,我不写那篇《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到今天我仍是一个清誉满满的财经作家,在千岛湖的小岛上隔岸点评。可是,我不会发现那只马桶盖背后的真相,不会推动新国货运动,不会调研数以百计的企业,不会做年终秀,不会走进那间热闹而危险的直播间。
你头上的白发、脸上的皱纹、身上涂抹和溅到的污泥,都不是平白而来的。上帝嘲笑每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是,如果没有那些人,也许人间不值得。
商业世界始终贯彻着人的多元性这一基本事实,并带有不容置疑的进步意义。其炫目喧嚣的表层,无法让这个镀金时代增加它的深度和批评力,甚至可能令很多人陷入浅薄的欢愉。但是,它以“纳米”般的细密度,让社会发生肌理层面的衍变。
这不是一个激烈的过程,有时候会让人变得对自己都非常失望。不过,我却相信,每一寸的进步都可能在未来挥发出预料不及的意义。
从在外滩吃到第一支冰淇淋蛋筒,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其实一直是一个记者。出人意料的仅仅是,在我写作的书籍中,我居然为自己独留了一个小小的、连我自己都很好奇的章节。
前日,一位《财经》记者小米采访我,问道:“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我答:“我希望三十年、五十年后,人们试图了解我们这代人的中国,在选择图书时,有一本侥幸是我的。”
“那么,你对自己的企业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它健康发展,做出好的知识产品,公司能上市,员工喜欢自己的工作,并因此过上体面的生活。”
“你会纠结吗?”
“会的会的,一直会的。”
年轻的小米看着我,好像也提不出什么有趣的问题了。她其实挺倒霉的,碰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老记者。
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冯迪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