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亚力克西·托克维尔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亚力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是卡尔·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在他们的动荡人生中,法国大革命既是相隔不远的当代史,也是他们学说的时代之锚。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托克维尔参与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出任内阁的外交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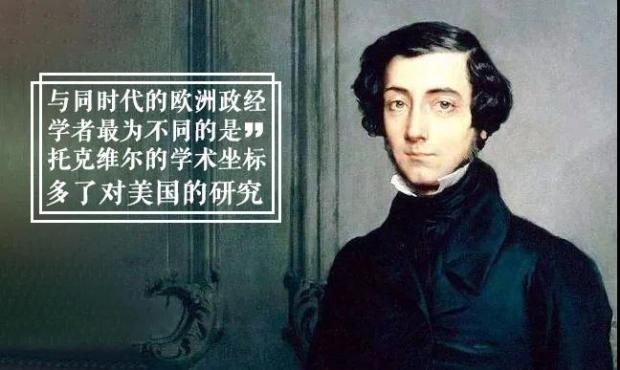
与同时代的欧洲政经学者最为不同的是,在托克维尔的学术坐标中多了一个新世界的维度,那就是对美国的研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是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是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们隔着一个大西洋,互相呼应,其思想的光芒迄今未熄。
1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与西方大约是画等号的,不过在经典的欧洲学者那里,美国是一个“他者”,甚至是一种癌症般的存在。
早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式的商业文明已经被欧洲知识分子所厌恶,被认为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温床。
1860年,爱德华·龚古尔——他因创办龚古尔文学奖而闻名——在评论新建中的巴黎城时就不无失落地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未来的美国的繁华都市。”这一情绪后来还被写进了一本法国的中学生历史读本中,作者督促欧洲青年思考:“美国正在变成世界的物质中心,欧洲的知识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 E·雅利菲耶,《历史通论》,1904年出版。

托克维尔出生于诺曼底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当过律师和法官,他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家族的贵族头衔。1831年,托克维尔还赴美考察。
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认真地研究美国,关于美国的学术资料十分稀缺,这倒给了托克维尔一个机会。他发挥实证调研的专业能力,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观察。《论美国的民主》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他的第一手接触和收集。
在邮轮到达港口的时候,托克维尔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入眼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激烈抨击,这让他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为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

在美国期间,托克维尔对三权分立下的政府运转制度进行了重点的研究,特别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制衡和分权模式,在他看来,“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托克维尔接触了很多民间的社团,从而对结社自由有了新的认知,他在书中写道:
各种政治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社团,甚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像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
事实上,托克维尔在此探讨的是一个正在生成中的现代公民社会的母命题: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作为一个来自大革命国度的青年学者,独立运动后的美国给予了托克维尔一个陌生的体验和观察视角。他很坦诚地自我解剖: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2
《论美国的民主》让30岁出头的托克维尔暴得大名,归国后的他成了国民议会议员,还是法兰西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在二十一年后,他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时的托克维尔,已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了,曾身处五个“朝代”,从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经历了议政、修宪、当部长、以“叛国罪”被逮捕等等的荣耀与挫折。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关注的主题仍然与青年时代的自己并无不同:民主、平等与自由,到底将以怎样的方式降临人间?
托克维尔首先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认为它是迄今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了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大革命的任务即便没有完成,它也已经导致了旧制度的倒塌。
他进而尖锐地分析认为,在法国,对自由的要求晚于对平等的要求,而对自由的要求又首先消失,结果要求获得自由的法国人最终加强了行政机器并甘愿在一个主子下过平等的生活。
在大革命时期,人们一次次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独裁者,却迅速地建立起更为专制的政权。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连这些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

托克维尔不无悲哀地写道:
看到中央集权制如此轻易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里,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托克维尔的分析并非凭空而论,就如同年轻时的自己,他查阅和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除了非常娴熟的政治领域之外,在涉及到经济制度的部分,他援引的原始资料,包括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国有资产出售法令和三级会议记录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第一代制度经济学家。
他的这些声音凌空而下,尖利而莽撞,并不为人们所喜,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就曾自嘲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3
托克维尔曾言:“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那么,为什么只关心当代的他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一再地阅读和讨论?
答案只能是——托克维尔的“当代”,也正是我们的当代。

正如同他所陈述的,物理意义上的巴士底狱会被一次次地攻陷和摧毁,但是人们心中的巴士底狱却可能更为顽强地一再重建。无论是新世界的美国还是老欧洲的法国,自由、民主与平等,从来不会很和谐地天然存在,它们之间甚至可能爆发难以调和的冲突。任何试图建设一个天堂的理想和主义,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奔向它的反面。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托克维尔的法国前辈罗兰夫人的呼喊穿越时空,百年以降,亚非欧美,各色人等,竟从未被证伪。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