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用爱和理想发功发电,但托举起整个大产业的,始终是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的驱动力。”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沸腾了!
随着导演饺子身上的爱马仕毛衣卖断了货,其执导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情人节的前一天,以突破100亿元的成绩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并冲进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前三。照此速度,2月14日圣瓦伦丁节过后,一举超过迪士尼的《冰雪奇缘2》怕是板上钉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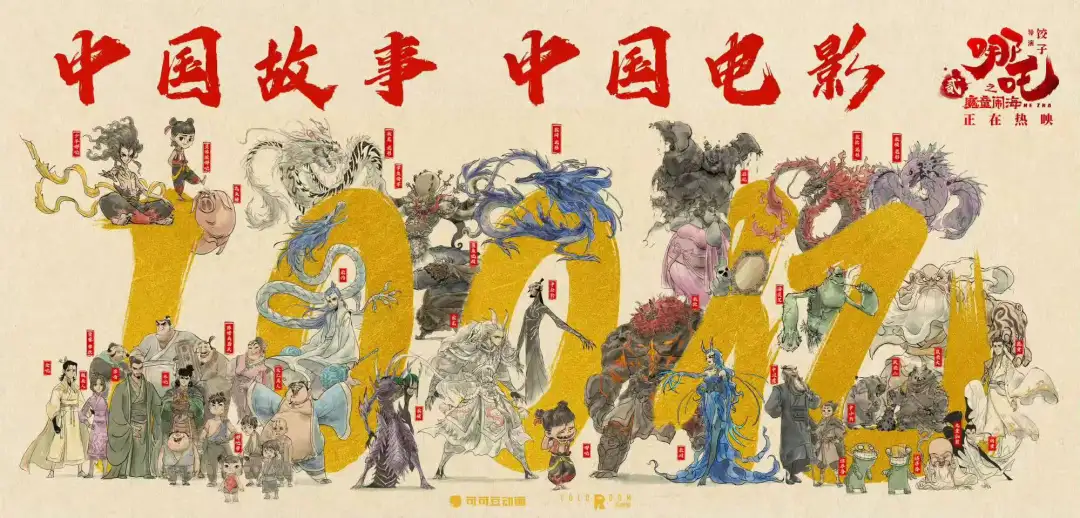
《哪吒2》票房破百亿海报
图源:微博@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哪吒2》是2025年开年继DeepSeek另一大现象级“产品”,票房突破100亿则是和DeepSeek登顶全球下载榜并列为中国新兴产业的“历史性时刻”。
托举起这100亿票房的自然是兴致沸腾的观众。
从春节首映到破纪录前,全国电影院见证了这股热浪般的情绪:某商场还是毛坯状况,楼上的电影院为上映《哪吒2》却早已装修得金碧辉煌;有电影院不惜24小时排片。
而就在昨晚,全网直播实时统计票房数据——俨然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全民狂欢。
谁是“托举者”?
《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100亿的背后,有一个数据惹人关注:它集结了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位国漫人参与,远超前作的1600人。
“工业化”是探讨《哪吒2》制作团队最绕不开的一个词。无可否认的是,动画是一个重工业,流程环节复杂,每一块运转这座庞大机器的“齿轮”,可能需要一位资深专家打磨多年。
所以对4000名专业人士和138家制作公司如元器件般的整合与协调,自然是将人才、技术、资金的“耦合效应”发挥到极致。
但这两个数字,首先意味着一次行业团结的大胜利。
饺子并非动画工业的第一位开拓者。2015年,田晓鹏主创的《大圣归来》,首次开启了对神话IP和中国动画工业化的探索,当年近10亿元的票房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他在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了整个行业的思考:“中国动画工业底子特别薄。一直以来,整个行业大家都在共享。本来我们就没法与国外进行技术上的抗衡,如果再各自为战,动画产业怎么发展?行业里的人本该抱团取暖。”
后来,我们看到了《白蛇》《长安三万里》《姜子牙》等动画特效的突破,从制作出每一根独立计算的“神采飞扬”的头发丝儿,到今天通过“绑定器”工具来完成哪吒削骨削肉的特效,其实都是行业技术共享和累积的结果。
然而技术研发只是“创新”这枚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更为复杂的工业化流程。像田晓鹏第二部大作《深海》中的渲染技术,落地就涉及复杂的跨流程的开发体系。
所以很多人把《哪吒》和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并称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两大里程碑”,是因为它们的背后,不仅是底层技术的相互影响和反哺,更代表着一套成熟、严谨的电影动画工业化流程体系在中国正式建立。
有趣的是,两位导演皆非科班出身,郭帆念的是法律,饺子读的是药学。如果说郭帆用法律的专业严谨规划中国科幻的叙事,那么饺子以医学的精准解剖中国神话的内核。
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用一种跨界式的工程思维革新了整个行业:以前的电影创作,很依赖于导演的艺术直觉,但新一代则用项目管理、数据分析和工作流,将创作转化为一项可量化、可复制的系统工程。
这或许是整个行业的心声。一年前斩获16亿票房的《姜子牙》的联合导演王昕感慨道:“我要改变中国动画人对个人的过分倚重,我要改变中国动画对流程的蔑视,我要改变中国动画用肌肉思考的坏毛病。”
因此,《姜子牙》动画采用了一种美国常用的“螺旋式迭代”方法:不是在一个步骤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而是同步推进多个制作环节,以体系化的方式共同推进项目。
毫无疑问,托举《哪吒2》100亿票房的,是138家动画公司和4000多位国漫人积累的底层技术,而托举起如今动画电影产业的,是一套新的工业化流程体系。
真正的托举者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又是谁托举起那138家动画公司和4000多位国漫人?
第一个答案是日本动画公司和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和普通制造业一样,电影动画工业同样符合全球化背景下专业分工和转移的规律——往性价比最高的地方流动。以电视动画为例,1960年代后,日韩承接了大量美国动画公司的外包工作。而到了1990年代后,日本的动画外包开始流向中国沿海地区。
2010年代后,日本海外分镜头动画产量占比增长到2/3。在电影方面,好莱坞特效和建模外包给中国公司在业内早已不是新鲜事,包括《2012》《阿凡达》《变形金刚》等在内的视觉特效大片。
可以说,动画电影行业的国际分工养活了一大批小工作室,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批动画人才,也为中国带来新的制作体系。但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大制作的战线铺得太长,难以让中国制作团队“旱涝保收”。项目需求少,也无法保证给团队充分“试炼”的机会。
这就不得不提影响中国动画公司饭碗的另一个产业:游戏业。
动画、电影和游戏,三个产业其实是不分家的,众多底层的革新技术和制作理念基本出自大型3A游戏公司。像王昕能为《姜子牙》带来新的创作理念和流程能力,是因为他曾在美国暴雪游戏供职14年,参与了几乎所有暴雪主力IP的动画短片(如《守望先锋》)。游戏圈有一句话是“用心做CG,用脚做游戏”,指的就是暴雪强大的动画制作能力。
特别是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团队的制作能力提升,诸如《艾尔登法环》等3A游戏的大量特效与建模都被外包给了中国。但是,3A游戏长制作周期的特点仍和动画电影类似,于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环境中,一群有能力供养这批小工作室的大金主出现了:氪金游戏。
所谓的“氪金游戏”,一般以网游、手游为主,玩家通常要花真金白银购买游戏中的虚拟产品以提升实力和体验,如道具、装备、皮肤等。
当然,许多中国家长嗤之以鼻,视其为“精神鸦片”,但它在产业端却拥有3A游戏和动画电影没有的优势:生产周期短,试错成本低,净利润率高。一般而言,头部单机游戏公司的利润率为20%,头部手游公司的利润率能高达40%,头部电影公司通常低于10%,投资不慎,动辄亏损。
托举起《哪吒2》的那4000位国漫人和138家动画公司,平时可能就排班、轮转于各个氪金游戏项目中,像宁波的点云文化团队,负责制作《哪吒2》的火球等2分钟特效,但在平时又参与《王者荣耀》的皮肤、腾讯和网易游戏的宣传片制作。
这群国漫人的“砍头日”更为紧迫,竞争者犹如繁星,经费可能遭多次“撇脂”,时常面对令人抓狂的反复审核与修改,但他们每一次对皮肤、特效、CP剧情、角色画像、CG的打磨,都为中国动画和特效行业的整体技艺的跃升按下了加速键。
《哪吒2》爆火后,不少外包公司在采访中分享了特效制作的“崩溃”的瞬间,这些瞬间或许“只道是寻常”——它藏在每一个突如其来且急迫的游戏项目中。正是它们的“折磨”与“供养”,让这群“星星之火”在残酷世界中卷出了一片天地来。
回报“托举者”
商业和经济是系统的,在黑盒中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我们可能难以想到一些曾让我们忽略甚至看不上的要素,会意外地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连接器。
正是无数股来自不同方位、或大或小的要素力量,形成了一股将《哪吒2》推向中国电影山巅的合力,你可以说它的成功是一次基于技术继承的必然,也可以说是一次基于爱国行为的偶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在这股合力中,确实有无数的人在用爱和理想发功发电,但托举起整个大产业的,始终是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的驱动力。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哪吒”吗?如果以悲观的视角看,下一部动画电影的特效可能更为炸裂,剧情更加出彩,但未必有《哪吒2》的人心凝聚力和票房号召力,那138家动画公司也未必在利益链上雨露均沾。那么剩下的命题便是:如何保证让行业从业者、那群“托举者”们能获得更稳定的收入?
其实当我们翻开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前十的史册,除了大名鼎鼎的《哪吒》《大圣归来》《姜子牙》等佳作,会发现居然还有四部是“熊出没系列”,分别是《熊出没·逆转时空》《熊出没·伴我“熊芯”》《熊出没·重返地球》《熊出没·原始时代》。这四部电影的制作周期几乎在一到两年,而整个“熊出没系列”IP成熟,有稳定的受众群体。
如果未来在动画技术稳中有进、流程和故事叙述保持良好水准的前提下,我们未必要呼唤下一部媲美《哪吒》的动画,行业反倒需要越来越多像“熊出没”这样的电影,甚至需要更多的以服务型游戏运营模式为主的大型游戏公司,因为当众多头部企业能为中下游公司稳定持续地创收、提供越来越多打磨技术的机会时,意味着一个良性循环的商业体系将会逐渐形成。
这或许才是回报“托举者”们的最好方式。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